https://new.qq.com/rain/a/20220120A05TE700
郭荆璞/文
近现代的金融史,不仅仅是一部关于金融危机的历史,也是关于通货膨胀的历史。在并不遥远的19世纪上半叶,多次发生的金融危机还是以通货紧缩为主的。然而随着信用货币大行其道,通货膨胀也在20世纪取代通货紧缩成为了更加普遍和杀伤力巨大的金融危机形式。
在21世纪,我们目睹了高就业率和低通胀的并存,甚至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试图解释“通货膨胀的终结”,就像他们也曾经在2008年之前试图解释新时代到来,经济周期已经被战胜一样。
莱因哈特与罗格夫在定量分析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特征时使用的5项指标包括了通货膨胀和货币汇率、银行危机、外债违约、内债违约,将这5项指标在每一年加总即得到当年的危机指数。就亚非拉区域而言,三个区域在二战前后都是危机指数的高点,而非洲在1994年,亚洲在1997年,拉美在1988年又是高点,尤其是拉美,其上世纪80年代末的高点明显超过了二战。亚非拉区域的金融危机当中,通货膨胀的影响非常明显。对于通货膨胀的分析,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而言,其重要性更超过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分析当中研究通货膨胀的意义。
通货膨胀与债务违约的选择变得更加复杂
在金属货币时代,通货膨胀时常以更隐蔽的形式出现,即发钞人有意识地降低货币中的贵金属含量。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期,货币中的贵金属含量都不足,幅度在5%以内的铸币税总体来说是非常公平的,然而历史上董卓铸小钱这样恶劣例子比比皆是,自汉至清,中国封建历史上中央政府有意滥发铜钱,造成物价暴涨万倍的例子也不鲜见。
那么中央政府为什么会推动货币贬值,会使通货膨胀率超过最大化铸币税的通货膨胀率呢?或者说,中央政府选择远高于任何可以由铸币税收入(产生于基础货币)解释的通货膨胀率这一悖论的目的何在呢?莱因哈特与罗格夫给出的答案是通货膨胀实质上是为了逃废债务,而不是铸币税本身。两位作者用数据说明了,对国内债务违约和外债违约发生前后,产出与通货膨胀轨迹进行对比,国内债务、国际债务、产出、通货膨胀,这四个最重要的指标的相互作用,可以看出政府对债务的态度,进而判断政府引导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如果通货膨胀的伤害过于剧烈,政府才会选择直接对债务违约。
换言之,单纯从基础货币创造的角度看待铸币税是不完全的,铸币税和通货膨胀共同构成了中央政府面临债务违约时选择政策的边界条件。
通过观察1500-2007年所有国家通货膨胀率中值的五年移动平均值,可以得到结论:通货膨胀率(中值)最后一次低于零是在大萧条期间,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和21世纪,我们要面临的主要的危机风险仍然来自于高企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代价剧烈,在国际资本市场还建立,或者债权人手段单一时,债务拒付的成本很低(还记得法国国王直接处死意大利债权人的例子吧)。通货膨胀并不是优先的选择,仅仅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时的备选,政府倾向于成本更小的债务拒付。随着国际资本市场越来越成熟,债权人的影响力和对债务的研究的深入,现代债务违约的案例在渐少,叠加信用货币的使用带来的铸币税,通货膨胀才成为了政府面临债务违约时更“好”的选择。
《这次不一样》书中给出了定量的关系,1900-2007年,通货膨胀危机(二战后高于40%年率,一战前高于20%)与外债违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9,1940-2007年是0.75,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府正在变得更加愿意同时依靠两种手段来减轻其实际利率的负担。通货膨胀与外债违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信用货币替代金属货币之后的现代性问题。
此外,债务违约,特别是外债违约之后,由于国际市场关闭和贸易收入锐减,政府往往无法应对日常开销而不得不诉诸通货膨胀或者指数化违约,即通过有意识的操控通货膨胀数据,来换取利率不跟随真实的通货膨胀上升。
两位作者的研究还指出了国内违约和外债违约过程中产出与通货膨胀的不同表现。国内债务违约之前4年,常见的是产出持续下降到违约;而国际债务则是常见先上升到突然下降到违约。国内债务违约前产出的下降通常明显大于外债违约前的产出下降,而且国内违约通常伴随着国内通货膨胀形式的违约,通货膨胀的程度远高于国际违约。
通过比较1800-2006年全球部分国家发生国内债务和外债违约的概率,莱因哈特与罗格夫绘制了国内债务和外债违约的相对比例,可以看到自1830年到1910年,大约80年的时间里面,政府的选择都是倾向于伤害国内居民小一点,而在战后到2008年,内外债违约概率在大多数时间保持均衡,只有在1970-1990年之间,外债违约的概率是明显高于内债的,政府无法让国内状况的本国居民承担太大的损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主要国家政府小心翼翼地避免国内债务违约,甚至不惜以外债违约的方式保护本国国民,但是这种保护的后果也十分明显。相比于国内债务的隐蔽和不那么显眼的痛苦,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看上去则惨烈得多。最重要的是,20世纪至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多发生的是银行危机,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尺度上都存在持续的不良影响,20世纪之前这样恶劣影响则更多来自于恶性通货膨胀。
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债务市场遭受到政府通货膨胀倾向(经常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严重摧残,国民比外国人更清楚不靠谱政府的通货膨胀倾向,这也是国内债务违约少的主要原因。
债券收益率曲线如果相当长的时间都保持平缓,甚至出现倒挂,市场会视之为异常状况,开始猜测经济基本面的可能恶化。然而两位作者也指出,事实上到世纪之交,资本市场才对短期债务越发偏爱,他们认为,这种偏爱是对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通货膨胀疲劳”的一种回应:通胀背景下市场更偏爱短期限的国债。
统治的力量通货膨胀能够实现国内主权债务违约,政府在这方面极具创造性;君主可以依靠强制国民实现对内违约,对外债则很难;货币扩张既可以通过稀释居民手中货币的价值实现财富转移,又可以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所以获得政府的青睐,一代又一代的投资者们,也正是带着“这次不一样”的幻想,投身于森林大海。
通货膨胀是一种税收
书中还列举了欧洲历史上的通货膨胀率极值年份,包括1521-1527年、1572-1587年、1621-1623年、1708-1709年、1757-1772年,新兴市场国家则数据缺失,通货膨胀的案例比比皆是。
根据莱因哈特与罗格夫的研究,1400-1850年欧洲的法币化过程,即使受到拿破仑革命的一定干扰,仍然体现出缓慢的变化,20世纪略有加速:1400-1800年之间贵金属货币以年化0.5%左右的速率贬值,而在拿破仑战争之前约0.3%,去世之后的之后约1.1%。
两位作者也指出,从数据来看,没有一个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成功逃脱高通货膨胀,而对其自身债务违约,也就意味着政府宣告,维持其本国货币得不偿失,或者是更便宜的以日用品赠送来试图换取民众对内债违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同时,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越来越高,已经超过了传统上的国际国内债务违约,也超过了高通货膨胀的概率。货币发行是垄断特权,垄断发展走向通货膨胀和对外贬值,最终被另一套垄断取代、革命,或者指数化(如“美元化”),货币垄断发行->滥用特权->超级通胀->货币和债务美元化,失去货币垄断发行权力,这样的戏码已经十分常见,不再展开列举了。
我们时常观察到,高通货膨胀使得居民在很长时期内,最小化其对未来宏观经济不当操作的风险暴露,也就是说,高通胀在很长时间内持续伤害国内居民的信心,也就降低了货币需求。
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我们都可以看到20世纪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多的以通货膨胀危机和以及银行危机出现。
我们站在新一轮通货膨胀的起点上吗?
那么当下呢?如果把2008年到2021年看作一轮仍然在进行当中的危机爆发和修复的过程,那么可以类比的是1929年到1945年的不太漫长但是极其痛苦的一段历史,二者皆有类似的背景,长达10-20年(1920-1929年与1980-2007年)的利率下降过程,资产价格泡沫的诞生和破灭(1929年与2008年),以及随后发生的利率降低到零附近的市场拯救行动。可以看到,在危机发生之后,美国的M0/GDP快速上行,在1931年到1936年间持续上升,到1936年经济出现好转之后美联储收缩货币,但自1938年之后又二次放水;同样在2008年到2015年,美国的M0/GDP再次持续上升,加息之后开始下降到疫情来临,巨量的救助计划形成了印钞的第二波狂潮。
在这种浪潮之下,1938年之后的10年,如果看大类资产的实际表现(剔除通货膨胀),股票(标普500指数或道琼斯指数的真实表现)几乎没有变化,房地产实际价格10年上升20%,唯有商品价格上升最为剧烈,10年间实际价格上涨超过100%。那么2020年同样站在第二波放水起点之上,我们又会从历史中找到哪些灵感呢?
通货膨胀掩盖违约,无疑是一种可能。
全球性金融危机早期预警
莱因哈特与罗格夫在《这次不一样》这本鸿篇巨著当中,以大量详实而且时间跨度惊人的数据构筑了自己立论的基础,也把本书打造成为一部优秀的研究数据集。
两位作者区分了全球传输过程中高速率或“快速而狂热”的跨国危机传递因素和低速率或“慢热型”的危机传递因素也区分了由共同因素冲击引起的模式,和从中心国家策源,通过共同贷款人渠道传染全世界这两种不同模式。直到本书的最后,两位作者终于搁下了掩面的琵琶,给出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定义。
莱因哈特与罗格夫为了给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个操作性定义,他们建立了描述金融体系动荡程度的综合指数,即金融危机指数(BCDI,0-5):系统性银行危机、货币危机、通货膨胀、外债违约、国内债务违约,这5种危机在某一年同时发生的数量加总,即为一国在特定年份的金融动荡综合指数。
全球性金融危机区别于地区金融危机和危害较小的多国金融危机,两位作者也给出了4种可能性:有中心国家出现问题;有2个或以上地区出现问题;每个地区有3个以上国家出现问题; GDP加权的金融动荡指数高于均值1个标准差。
这样两位作者完成了他们对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定义。
依据这样的定义,我们可以更加完整的总结金融危机的前兆:资产价格显著上升;实体经济活动减缓;大额经常项目赤字;持续的债务累积;持续性资本流入和金融自由化。一个国家的国内/国际债务、产出和通货膨胀,是判断金融危机即将到来与否的主要指标。当这些指标指向金融危机的时候,如果资本市场上流传着这样的信念,相信金融危机已经被消灭的信心滋长,相信“这次不一样”的时候,金融危机也就不远了。
两位作者还特别提到,住房价格的周期性波动是金融危机的核心元素,二者有着很大的相关性。一般来说,持续性的资本流入导致单方向的信贷扩张,而信贷扩张几乎总是导致最终的泡沫破裂和危机降临。与资本流入和信贷扩张伴随的,常常是投资性房地产价格的周期性变化,和对价格上涨趋势永远持续的错误幻想。当永远涨的幻想遭遇周期,泡沫破裂的风险就会极度放大。
在书中列举的数字中还可以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的两个特征,首先是几乎所有宏观经济和金融时间序列数据,包括收入、消费、政府开支、利率等,新兴市场国家都表现出更高的波动性,而只有房地产,这一最本地化的资产价格与是发达国家的波动是一致的,这反映出新兴市场国家的房地产本质上是投资品而不是消费品;其次是由于数百年尺度上商品价格明显地向下漂移,更加依赖初级产品的新兴市场国家在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时候更脆弱,也就不足为奇了。
通过分析和寻找金融危机的早期预警方法,我们会发现,宏观经济理论处理的是正常阶段的经济,对危机可能无效,因为那些校准到统计上“正常”年份的宏观经济模型,事实上是把危机出现的时刻作为“异常”处理掉了的。模型损失了那些真正能够预警的因素。
由于战后银行危机在金融危机中占比的提升,作者还列出了战后特别是五大危机当中,实际房价、实际股票价格、经常账户余额与GDP之比、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基于购买力平价),以及银行危机与中央政府实际负债之间的关系,并且重点分析历史房价数据,把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作为危机开始和结束时间点的最可靠的指标。
为了研究全球性金融危机,还需要两类全球性变量,第一类是能覆盖全球经济的基础变量,例如世界商品价格;第二类则是真正的具有全球影响的核心经济金融变量,例如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利率和美国长期国债利率。
试图建立危机早期预警系统,建立在危机数据与一般宏观经济数据不同的底层数据之上是否可行?莱因哈特与罗格夫在本书的末尾给出了他们心目中已经或者可能摆脱连续违约踏入“靠谱”国家序列的备选,遗憾的是,2010年的他们选入了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意大利,几乎马上就被“欧猪五国”的组合打脸。事实又一次告诉我们,连研究“这次不一样”最深入的专家,也会在试图回答“谁会不一样”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失前蹄。
金融危机是一个永恒的现象,资本流入和杠杆化总是给人信心,超越常识的边界,给出“这次不一样”的解释,直至危机发生。融资人和贷款人,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都会自我欺骗,这是周而复始的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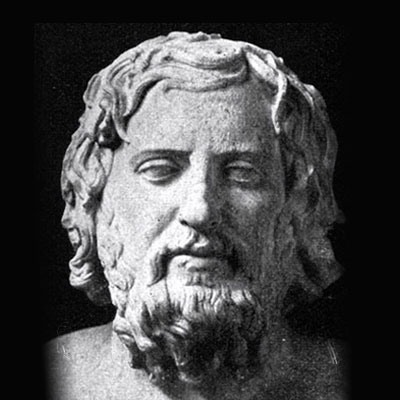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