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来,阳明心学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一门显学,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自媒体及普通大众所关注、研讨及传播,尤其是在企业界,学习阳明心学已经蔚然成为风气。然而,阳明心学到底说什么,它是怎么发生、发展并完成的,大部分学习者还是不甚了了。对“龙场悟道” 许多学习者尚耳熟能详,但对“天泉证道”却知之甚少,以至于对阳明心学不能够全面、立体地理解与掌握。本文试图从“龙场悟道”到“天泉证道”,按照时间脉络系统梳理一下阳明心学是如何发端、完善、成熟和完成的,以帮助学习者能够更加系统、全面地了解把握阳明心学。
1“龙场悟道”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要系统梳理介绍阳明心学,不得不从先秦时期的传统儒学——孔孟之道说起。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传统儒学,那就是孔子所说的“仁”;如果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仁义”。 文天祥在就义前所留下的临终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就是对“仁义”的最好阐释。用孔子自己的话说,“仁”就是“爱人”,就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仁”和“礼”。“仁”就是要求君王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礼”就是用“正名”(即等级制度)的方法建立社会秩序,即“和谐社会”。“内圣外王”是传统儒学的基本纲领和终极追求,是成为儒家“圣人”的必由之路。先秦时期,儒学只是众多学说中的一种而已,并未获得各国君王的重视。
到了汉代,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此作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治国之术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但是,到了隋唐时期,佛、道开始盛行,传统儒学面临了极大的挑战。佛教徒居然史无前例地提出了以佛为正,儒道为邪,三教归佛(又称“三教合一”)的主张,而儒家学者则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唐代初年,统治者奉行以道为主的三教并行政策,传统儒学自汉代以来的道统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到了北宋,由于宋王朝“半部论语治天下”,儒家学者开展了大规模的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了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而非“仁”)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理学其实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产物(当时佛教已经大致完成了融合儒道的中国化过程),是儒家思想汲取道家、玄学、禅学思想的精华,并注入了哲学思辨的因子,是囊括了天人关系而形成的更为理性化、思辨化的思想体系,被称为“新儒学”,以区别于孔孟之道的传统儒学。朱熹的思想,与二程(颢、颐)的思想合在一起被称为“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认为,由于“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就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这就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对《大学》八条目中“格物致知”的解释。朱熹是以“道问学”的思路解释“格物致知”的:格就是推究,物就是天下万物,致就是求得,知就是知识,也就是推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朱熹说:
“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
朱熹认为,儒家圣人的实现路径就是“内圣外王”,就是《大学》开篇的“三纲领八条目”: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中,“修己”就是“内圣”,是“治人”的前提,“格致诚正修”就属“内圣”的范畴,“内圣”就是通过内在修养成为圣人的一门学问,人格完善的过程就是以天理主宰人心、转人心为道心的过程;“齐治平”属“外王”范畴,“外王”就是以圣人之道在社会治理中推行王道、创造和谐、大同社会(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敬妇从、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以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在王阳明之前,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就是由朱熹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到明代时,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和束缚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王阳明从小就立志要成为儒家的“圣人”。钱德洪的《阳明先生年谱》记载:
十有八年(成化)壬寅,先生十一岁,寓京师。尝问塾师曰:
“何为第一等事?”
塾师曰:
“惟读书登第耳。”
先生疑曰:
“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王阳明在十一岁时就为自己立下了读书做圣人的宏伟志向,但到了十八岁时“始慕圣学”。《阳明先生年谱》记载:
二年(弘治)己酉,先生十八岁,寓江西。十二月,夫人诸氏归余姚。是年先生始慕圣学。
先生以诸夫人归,舟至广信,谒娄一斋谅,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遂深契之。
在当时的理学大师娄谅的指导下,王阳明也认为“圣人必可学而至”。到了二十一岁时,王阳明开始了朱熹的“格物致知”之学。《阳明先生年谱》记载:
五年(弘治)壬子,先生二十一岁。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
先生始待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
格竹失败,对青年王阳明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开始对自己能否成为“圣人”的志向产生了怀疑,于是转入了“辞章之学”,才名一度享誉京城。
2龙场悟道
“阳明格竹”这一文化事件看似荒唐,但却是王阳明与程朱理学分道扬镳的分水岭。36岁时,王阳明因坚持圣人理想而与太监刘瑾集团发生冲突被贬贵州龙场,在绝望的境地上竟然发生了“龙场悟道”事件。《阳明先生年谱》记载:
三年(正德)戊辰,先生三十七岁,在贵阳。春,至龙场,先生始悟格物致知。
···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王阳明在龙场“始悟格物致知”,悟到了“圣人之道”就在我们的内心,过去按朱熹所指引的向心外求索“圣人之道”的“格物致知”之路走错了,并用默记的《五经》印证“莫不吻合”,于是,以“心即理”为逻辑起点的阳明心学便横空出世了。
王阳明是这么理解“格物致知”的,所谓“格”就是“正”,所谓“物”就是“事”,所谓“致”就是达致,所谓“知”就是“良知”。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
王阳明还补充解释说:
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可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
王阳明强调自己的“格物致知”之学是“实学”,需要在事上磨练。《传习录》记载:
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
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
另外,在王阳明那里,“心即理”、“性即理”都是一个意思。他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就说:
心也,性也,命也,一也。
王阳明说:
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传习录拾遗》)
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说个心即理是如何,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故便有许多病痛。(《传习录》)
王阳明反复强调,吾心便是天理,便是世界的本体,它既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又是事物变化的归宿,“心外无物,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提倡 “求理需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如果心有主(良知),则我制外;若心无主(良知),则外制我,心为本体,万物在我。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了。既然人人内心都有“良知”,为何又会干出禽兽不如、是非不分的事情呢?王阳明认为问题出在知行不合一上,于是,从来年的贵阳讲学一直到49岁这段时间内,王阳明讲学的重点都是讲“知行合一”。《阳明先生年谱》记载:
四年(正德)己巳,先生三十八岁,在贵阳。提学副使席书聘主贵阳书院。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
于是,王阳明所求索的“圣人之道”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过去依娄谅“圣人必可学而至”的向外求索之路,转而现在向内求索,走上了唤醒良知、知行合一之路。而且,在“知行”关系上,王阳明认为“知行”不可分,认为“知易行难”,认为“知而不能行,只是不知”。《阳明先生年谱》记载:
徐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决于先生。先生曰:
“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体。”
王阳明的妹夫兼弟子徐爱没有搞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王阳明便举“孝悌”为例,说某人知孝知悌一定是指某人已经在行孝行悌,就像夸一个人懂礼貌,一定是这个人在行为举止上非常有礼貌,而不是指这个人能说出关于礼貌的大道理。所以,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知行合一之学,吾侪但口说耳,何尝知行合一邪!
“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继“心即理”后的第二个核心命题,是“圣人之道”的唯一实现途经。在阳明心学的语境中,真正的“知”里面必然包含了“行”;真正的“行”里面必然也包含了“知”。知(良知)是行的主导,行是知(良知)的体现;知是行的开端,行是知的完成;知中含行,行中含知。知和行本是一回事,是相互依存的,不能相互割裂,真知就是行,不行不足以为知。王阳明认定真正的“知”,是必定要落实在“行”并且已经在“行”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王阳明所说“知行合一”的“知”的核心内涵首先是“良知”,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四端之心中的“是非之心”,是道德导向的,是每个人原本就具有的;其次是“认知”,也就是“见地”(智慧),具有可知性,就是《传习录》中所说的“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再次是“志向、目标”,是结果导向的,具有可求性。“志”是“立志”,是终极目标,不是过程,所有行为过程要对结果负责任。为了达至终极目标,在“良知”的指导下是可以“法无定法”的,有道是“心有正邪,法无正邪;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也邪”。王阳明平定匪患和宁王叛乱所采用的各种手段,就完美地诠释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
王阳明强调的知行一体、不分先后,也是针对朱熹“知先行后”观点提出来的。朱熹讲“论先后,知为先”,这无形中给人们借口未明理而不干实事大开方便之门。王阳明说,我的知行合一是一副对症的药,此药专治这种“知先行后”的流弊的。可见,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重点是放在“行”上的。故作为阳明后学的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姚江学案》中说:
阳明先生“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
但到了50岁时,王阳明的讲学内容开始发生变化,专讲“致良知”,用“致良知”来含括“知行合一”。《阳明先生年谱》记载:
十有六年(正德)辛巳,先生五十岁,在江西。正月,居南昌。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
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乃遗书守益曰:
“近来信得致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今经变后,始有良知之说。
王阳明为何突然从“知行合一”讲到“致良知”了呢?王畿在《王畿集》中记录下了老师王阳明的这么一段话:
吾于平濠之后,致知格物之学愈觉明彻。···大都世间毁誉利害,不过一身荣辱,一人得失。吾所遭谤···蒙以灭族无辜之隐祸···
清人费纬裪编的《圣宗集要 卷六 王守仁》中也记载:
(王阳明)诛宸濠后居南昌,始揭“致良知”之学,曰:
圣人之学,心学也。宋儒以知识为知,故需博闻强记以为之;既知矣,乃行,亦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圣贤教人,即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于是举《孟子》所谓良知者,合之《大学》致知,曰致良知,以真知即是行,以心悟为格物,以天理为良知。
由此可知,王阳明是在平定宁王因功得祸后开始讲“致良知”的。从龙场悟道到平定宁王这段时间,王阳明在提倡“知行合一”时认为“知”的含义是多层面的:良知、认知、志向。但平定宁王之乱后,王阳明本人所遭受到的种种不公,让他深刻认识到“知”的核心含义应该是“良知(是非之心)”,而“行”则应该专指“致良知”的行为,“致良知”才是实现“良知”、成为“圣人”的唯一途径。于是,王阳明晚年在绍兴讲学期间便专讲“致良知”。王阳明在《传习录 答顾东桥书》中说: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
所以,到了50岁左右,王阳明经过平定江西匪患及宁王叛乱这些事上的磨练,回归绍兴老家后讲学之风就为之大变了,开始在稽山书院及伯府第、阳明书院中专讲“致良知”之学,认为能否“致良知”是能否成为圣贤的唯一标准。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
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
良知这个概念并非王阳明的首创,而是来源于孟子的“良知”说。孟子的“良知”是和人的具体心理活动结合在一起的,比如“恻隐之心”,指人的同情心;“羞恶之心”,指人的荣誉感和羞耻心;“恭敬之心”,指人在处理伦理关系时尊老敬长之心;“是非之心”,指辨别是非的能力。孟子把这四种“心”叫做“仁、义、礼、智”四端之心,认为它们就是“良知”的基本内容,人所有的道德行为都是由这四种道德意识的萌芽扩充而来的。而王阳明所认为的“良知”,最重要的就是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是人人都有的。是非之心,这是不用思考就能知道,不用学习就能做到的,所以叫做良知。良知就是先天具备的判断是非和选择善恶的道德标淮,故王阳明常常把“良知”比喻为“明镜”。王阳明认为,良知就是内心本有的“灵昭明觉”,就好像一面明镜,容不得任何一点细微的障蔽。不管是美的或丑的东西,“明镜”(良知)一照就会现出原形。故良知能够辨别善恶、知是知非,“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传习录》),而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力量作为主宰。王阳明在平定宁王叛乱后所遭受的种种不公,皆是朝中奸佞权贵良知缺失的结果。
“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继“心即理”、“知行合一”后又一个心学命题,也是对“知行合一”理论的概括与升华。“致良知”也就是把“良知”扩充、推及到万事万物之中予以发扬光大,从而将人的潜在道德意识转化成现实的人生价值(在事中修行)。王阳明认为,良知之学是开启人心道德的钥匙,只要唤醒天下人,使人人自“知”其本心的“良知”,自“致”其本心的“良知”,彻底改变杜会“善恶不分”的道德风气,则乱世可救,天下便可实现“大同”。
王阳明认为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能够“致良知”这一命题的逻辑前提是“万物一体之仁”。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
概括地说,阳明心学实质上就是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经世致用”为为学目的的良知心学。王阳明从三十七岁龙场“悟道”(心即理、知行合一)到五十岁始揭“致良知”之教,标志着阳明心学的完善和成熟。王阳明甚至提出“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的观点,这对人的个体价值的确认不亚于同时期西方的文艺复兴。
3天泉证道
1528年秋,56岁的王阳明即将从绍兴越城赴两广平叛。此时,晚年的王阳明又对他的“致良知”之教作了最后的总结和“判教”,也就是“良知四句教”,史称“天泉证道”。四句教的内容是这样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简单地说就是:心之本体是无善无恶的,意念产生(相当于佛家讲的“发心”)就有善有恶了,而对善恶的判断辨别要靠自己内心的“良知”,为善去恶就是格物(王阳明解释“格”就是“正”,“物”就是事),就是致良知。
也许是朝廷留给王阳明的时间太少了,王阳明还没来得及说透自己的“四句教”就匆匆赴两广平叛了,从此再也没能活着回到绍兴,这后来就导致了阳明后学的分化。清华国学院陈来教授在他的《有无之境》一书中就说:
“四句教”关系着阳明思想的“终极关怀”和基本宗旨,而且,不阐明四句教也不可能彻底了解阳明的“良知”学说。从历史的角度,四句教也是了解阳明晚年思想发展的核心课题。
“天泉证道”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在1528年(嘉靖六年)秋,王阳明即将从绍兴启程赴两广平叛。这年9月8日这天夜里,王阳明的两位大弟子王畿和钱德洪,因对王阳明的“四句教”理解不同而产生了分歧,故相约侍立于伯府第碧霞池天泉桥上,待客散后向老师王阳明讨教“四句教”,这就是发生在明中期绍兴伯府第碧霞池天泉桥上中国文化史上非常著名的 “天泉证道”。 对于“天泉证道”事件的记载,目前最权威的版本还是王门弟子都认可的《传习录》、钱德洪编的《阳明先生年谱》和王畿的《王畿集》,以当事人钱德洪和王畿的记载最为全面,也最权威。我们按照刊行的时间顺序来还原一下“天泉证道”事件的本来面目。
刊行于嘉靖34-35年(1555-1556年)的《传习录 卷下》是这么记载的: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复征思、田 。将命行时,德洪与汝中论学。汝中举先生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德洪曰:“此意如何?”
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 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
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
是夕,侍坐天泉桥,各举请正。
先生曰:“我今将行,正要你們來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瑩无滯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 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 是我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
既而曰:“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這話头,隨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顔子、明道所不敢承当,豈可轻易望人?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 可不早说破。”
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刊行于嘉靖42年(1563年)钱德洪(1496—1574年)编撰的《阳明先生年谱》是这么记载的:
是月(九月)初八日,德洪与畿访张元冲舟中,因论为学宗旨。畿曰:“先生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话头。”
德洪曰:“何如?”
畿曰:“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有恶, 毕竟心亦未是无善无恶。”
德洪曰:“心体原來无善无恶,今习染既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若见得本体如此,只说无功夫可用,恐只是见耳。”
畿曰:“明日先生启行,晚可同进请问。”
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将入内,闻洪与畿候立庭下,先生复出,使移席天泉桥上。德洪举与畿论辩请问 。
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问。我今将行,朋友中更无有论证及此者。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
德洪请问。
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饐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气力?德洪功夫须要如此,便是合得本体功夫。”
畿请问。
先生曰:“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难遇。一悟本体,即见功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此顔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二君以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
畿曰:“本体透后,于此四句宗旨如何?”
先生曰:“此是彻上彻下语,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功夫。初学用此,循循有入;虽至圣人,穷究无尽。尧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
先生又重嘱付曰:
“二君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识以来,已为习俗所染, 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著实。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以不早说破。”
是日洪、畿俱有省。
刊行于1587年的《王畿集 卷一 天泉证道记》是这么记载的:
阳明夫子之学,以良知为宗,每与门人论学,提四句为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学者循此用功, 各有所得。
绪山钱子谓:“此是师门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
先生(王畿)谓:“夫子立教隨时,谓之权(变通)法,未可执定。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
绪山钱子谓:“若是,是坏师门教法,非善学也。”
先生谓:“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根转。若执著师门权法以为定本,未免滯于言詮, 亦非善学也。”
时夫子将有两广之行,钱子谓曰:“吾二人所见不同,何以同人?盍相与就正夫子?”
晚坐天泉桥上,因各以所见请质。夫子曰:
“正要二子有此一问。吾教法原有此两种: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世间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见,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见,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颜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说破, 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 然此中不可执著。若执四无之见,不通得众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无从接授;若执四有之见,认定意是有善有恶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无从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 虽已得悟, 不妨隨时用渐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圣,所谓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 正好保任,不宜轻以示人,概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须进此一格,始为玄通。德洪资性沈毅,汝中资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为善学耳。”
自此海内相传天泉证悟之论,道脉始归于一云。
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是:
1,《传习录》和《年谱》中没有“四有”“四无”的说法,此说法出自王畿(1498年—1583年),而非钱德洪(1496年—1574年);
2,四句教首句指本体,后三句指工夫。四句教对“上根之人”或“下根之人”都是“彻上彻下”工夫,因为四句教即顿即渐,即有即无,即上即下,即本体即工夫,故才可以说是阳明心学的最后判教。
3,四句教讲的是渐修功夫——致良知;王畿讲的四无教是顿悟之法,有把 “致良知”之说推向禅学之嫌。黄宗羲就批评王畿近于禅老而致使王守仁之学渐失其传(《明儒学案》卷十二)。但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却将批评矛头指向了王阳明,认为“天泉付法,止依北秀(指神秀)南能(指惠能)一转语作葫芦样”,说王阳明是在模仿禅宗。
从以上三篇记载就可以看出,王阳明晚年提出的“良知四句教”,在他去世前弟子们的理解就有分歧,以他的两大教授师弟子钱德洪、王畿(类似禅宗五祖宏忍的两大弟子神秀和慧能)为代表。钱德洪坚守“四有说”,类似神秀走“渐修”之路;王畿倡导“四无说”,类似慧能走“顿悟”之途。两人争执不下,才有在王阳明临行前再次求教王阳明的“天泉证道”这一事件的发生。
王阳明本想调和两人的观点,说王畿的“四无说”是接引“上根之人”(佛家语)的,但“上根之人,世亦难遇”,“此顔子、明道不敢承当,豈可轻易望人”?“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若执四无之见,不通得众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无从接授”。而钱德洪的“四有说”是接引“中下根之人”的,“世间上根人不易得,(王阳明)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 通此一路”,“不妨隨时用渐修工夫”。最后王阳明强调:
“我年來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
从王阳明的语意里不难看出,“良知四句教”及阳明本人的“立教”就是为“中下根之人”立的,用以接引及教化大众,还是要用“四句(有)教”。虽说不否定王畿,但语气里是肯定钱德洪的。但遗憾的是,王畿虽“有省”,但仍坚持自己的“四无说”。
为此,钱德洪、王畿隔天又追送王阳明至严滩,继续求教于王阳明,这就是著名的“严滩问答”。《传习录 卷下》记载: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与汝中追送至严滩。汝中举佛家“实相幻相”之说。先生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工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说本体。”先生然其言。洪于是时尚未了达,数年用功,始信本体工夫合一。但先生是时因问偶談,若吾儒指点人处,不必借此立言耳。
《王畿集 卷二 绪山钱君行状》记载:
夫子赴两广,予与君送至严滩。夫子复申前说,二人正好互相为用,弗失吾宗,因举“有心是实相,无心是幻相;有心是幻相,无心是实相”为问。君拟议未及答,予曰:“前所举是即本体证功夫,后所举是用工夫合本体。”夫子莞尔笑曰:“可哉!此是究极之说,汝辈既已见得,正好更相切劘,默默保任,弗轻漏洩也。”
二人唯唯而别。
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徐阶(1503年 -1583年,聂豹的弟子,明嘉靖后期至隆庆初年计除严嵩后任内阁首辅)撰写的《龙溪王先生传》记载:
既而有叩玄理于文成者,文成以“有心无心,实相幻相”诏之。公从旁语曰:“心非有非无,相非实非幻。才著有无实幻,便落断常二见。···文成亟俞之。”
“严滩问答”里的“心”指心体,“实”指真实、存在,“幻”指虚幻、不真实、不存在。“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从本体上说工夫(用);“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从工夫上说本体。王阳明是要求钱、王二人不要执着于心体是善是恶、是实是幻的两端,就如同《金刚经》所说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但王畿还是借用禅宗的“实相无相、即空即有”之意,来坚持自己“四无”的观点。王阳明并不否认王畿的说法,但认为“有无之间,不可以致诘”,希望王畿“默默保任”(佛家用语,涵养真性而运用之),“弗轻漏洩也”(王畿后来还是漏洩了)。王阳明是希望钱德洪不要太执着于“有”,王畿也不要太执着于“无”,“二人正好互相为用,弗失吾宗”。但两人最终还是各执一端,让九泉之下的王阳明“失望”,这也直接导致阳明后学的分歧。
那王阳明晚年为什么要在“致良知”之外又来个“天泉证道”呢?我认为王阳明是要用《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来印证自己的“良知心学”这一“圣人之道”,就如同“龙场悟道”后他用“五经”来印证自己的“格物致知”和“心即理”一样,以完成自己“致良知”心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统一。所以,“良知四句教”就是对《大学》“心-意-知-物”(内圣)的具体阐述和逻辑自洽:
由此可以说,王阳明晚年“天泉证道”(良知四句教)是阳明心学成熟和完成的标志。这也说明,王阳明晚年的思想经过几变不偏“有”也不落“空”,回归于儒家中道,并因此一举超越了他的前辈陆九渊和陈白沙,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这也正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 卷十 》中说的: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 老 ···及至居夷处困,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居越以后,所操益熟。
稽山书院 2024年09月10日 09:07 浙江
https://mp.weixin.qq.com/s/A-lNu-Q_C_hhl2ubN50Uo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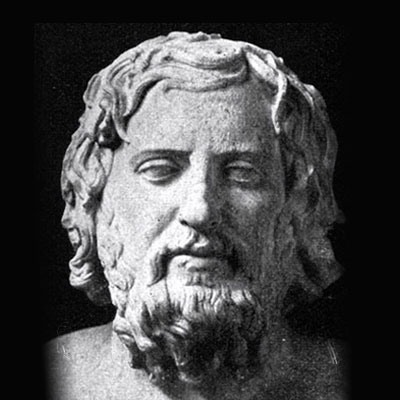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