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忠民,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来源:《福建论坛》2012年6期
整个西方哲学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当代的发展,其间经历了几次重大转折。其中,特别令人关注的是:有关先验与经验之争,因为先验与经验之争其思路及其解决途径直接关乎合理性与合法性之争、理性与非理性之争。
康德实现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颠倒了对象决定认识,认识反映对象,这种传统的认识模式,强调并突出了主体设定、规范对象的绝对主体性地位,将认识解读为先验(范畴)统摄经验(材料),但却将认识严格地限制在经验的现象界。尽管康德竭力调和先验与经验之争,并竭力消解前人将认识对象实体化、对象化的倾向,但最终却加深了先验与经验之间的沟壑,并导致了超验的本体界与经验的现象界的对执,实际上,将超验的本体界宣布为不可知。在康德那里,合乎先验的东西就是合理的,但是合理的未必合法,因为在先验与经验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合理性与合法性是相互割裂的。同样是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代表的黑格尔,在康德生前就酝酿了对康德哲学的变革(康德死于1804年,黑格尔在1806年完成《精神现象学》书稿)。黑格尔试图由经验(前逻辑学即现象学)超入先验(逻辑学),再返还到经验(应用逻辑学即法哲学、历史哲学)之中,并将康德一次性设定的先验原则变革为范畴、概念的自我否定、自我设定的矛盾运动。黑格尔对于经验的解构更是独树一帜,他将经验解读不只是为自己而且也为对方不断产生对象的辩证运动①。黑格尔建立了先验与经验的和解与统一,消解了两者之间的沟壑,并通过对“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这种原则的贯彻,将合理性与合法性统一在一起。在黑格尔那里,作为合理性来源的先验的东西,不再是高高在上而脱离经验的现实,而是通过经验的运动来表达自己,并在经验中实现自己,与经验王国中的合法性相互结合在一起。
但是,黑格尔对康德所实行的变革和改造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却受到后人的质疑。因为,黑格尔又恢复了逻辑的本体论地位,而将理性与逻辑实体化,并超出认识论范围,将其宣布为一切的一切之根据和本质,从逻辑这种先验的东西里推演出经验世界中的一切,黑格尔将康德的规范性的逻辑篡改为构造性的逻辑,僭越了理性的界限,俨然成了无所不能的上帝。显然,黑格尔所实现的先验与经验的和解,最终还是以先验凌驾于经验之上为前提的。而黑格尔所谓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统一也实际上就是,凡是符合逻辑必然性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也就是合法的。而当黑格尔进一步论证合法的也就是合理的时候,他已陷入了循环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无限事物(如上帝)区别于有限事物就在于它超出了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对立。黑格尔的论证无法逃脱安瑟尔谟有关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之魔掌。
德国古典哲学之后,不只是黑格尔对康德的改造受到质疑,而且,就连包括康德、黑格尔在内的整个西方理性主义哲学都受到批判。如前所述,尼采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理性主义哲学那里,世界之所以是理性的,表现出逻辑性,是因为世界事先已被人为地理性化、逻辑化了。以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对所谓的先验原则,逻辑必然性等等发难,而视之为人类思想的虚构。尼采不只是批判先验原则脱离经验之无效、荒谬,更是揭露先验逻辑的盛行使人类文明的发展误入歧途,导致了人类优秀本能的衰退和文化的腐败。尼采要告诉后人,惟有有助于人的优秀本能的东西才是合理的,才是合法的。从而宣布了整个传统的理性主义所倡导的先验性的东西的非法性与“不合理性”。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对传统的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并非彻底,他称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海德格尔认为,尼采于摧毁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原则、先验逻辑这种绝对本质和基础后,又确立起新的绝对的本质和基础,只是尼采用非理性、非逻辑的权力意志、超人加以替代而已,他仍然要为一切的一切寻找一个超出一切经验之上的“先验”的、无条件的支点和根据,尼采对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追求与论证与前人的思路也并无二致。海德格尔彻底摒弃了前人竭力为经验寻求先验根据,为先验填充经验材料的做法,而强调人的存在乃是一种“在世之在”(In-der-Welt-sein),②存在者的存在的根据,就在其自身的存在,哲学就是要追问使存在在起来的存在。
但是,海德格尔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也并非彻底,在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眼中,海德格尔依然是形而上学哲学家,因为海德格尔并未真正彻底地超出先验与经验之争,还是有追求先验的根据与基础之倾向,要真正解决先验与经验之争,就必须完全放弃先验的幻觉,彻底解构本质、基础、中心等概念,怎样都行,没有普遍适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标准。上帝死了!人也死了!哈贝马斯坚持现代性而对抗后现代主义,他对后现代主义一些代表人物德里达、利奥塔、布尔迪厄、福柯等人要彻底解构基础、本质、中心的做法,进行了批判与抵制,哈贝马斯要从先验走向经验,从先验哲学、意识哲学里走出来,走向社会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他要用交往合理性取代传统的合理性,并对现当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显然,整个西方哲学有关先验与经验之争,不仅构成了其哲学发展转型的主线索,更为重要的是从中折射出以黑格尔为轴线,前黑格尔与后黑格尔哲学家走出先验与经验之争的陷阱的努力与苦恼。
一、黑格尔对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批判
黑格尔为了更明确地将自己的逻辑学区别于前人的逻辑学。表达出他的逻辑科学的思辨性,对唯理主义哲学与经验主义哲学进行了批判,揭露了这两种哲学在先验与经验及其两者相互关系上的失足与缺陷。
黑格尔认为,以笛卡儿为代表的唯理论,固执于人类认识形式的先天性,为了获得所谓认识的逻辑必然性,而忽视了感性经验材料,从而导致了在认识论方面的空虚和抽象的特征,并具有很浓厚的独断论的倾向。黑格尔指出:“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以为思维的规定即是事物的基本规定……凡是思维所想的,本身就是被认识了的东西”③。唯理论以为只要凭借从纯粹先验的逻辑出发,就可以毫无疑问地把握现实事物,从先验的原则可以直接推演出经验的东西,而不问这种一次性的先验的东西其合法性何在,它作为经验的东西的根据,其合法性或根据何在,也不问先验的东西何以能够与经验的材料相结合,而只是坚守着“思维的规定即是事物的基本规定”这种抽象、空洞的信条。因此,唯理论于坚持先验的东西的绝对的优越性的同时,就造成了哲学认识的重大欠缺,也即缺乏具体的内容,缺乏坚实的据点。正是唯理论在认识论的这两方面的欠缺,“有助于引导哲学思想趋向于经验主义”。与唯理论不同的是,经验论不是从先验的东西,不是从思想本身去寻求真理,而是“从外在和内心的当下的经验中去把握真理”④。经验哲学内部有关经验的理解和运用不尽相同,但是却都强调人类的认识与行为必须以经验为出发点,并都把经验看作是当下经历的某种独立于经验者的被给予性的东西。黑格尔指出:“经验主义中有一重大原则,即凡是真的,必定在现实世界中为感官所能感知”⑤。经验论较之唯理论更为注重现实,切合实际。正因如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唯理论坚持从先验的东西出发所带来的缺乏具体内容和缺少坚实据点的局限。但是,经验论却由此陷入了自身的无法克服的困难,也即不能满足人类精神追求无限性或无限对象的要求和追求普遍必然性的要求。因为,经验主义原则的彻底贯彻,势必要将其内容仅限于感觉经验的范围之内,仅限于有限事物,而否认一切超感官的事物,并否认人类有认识它们的可能性,而“只承认思维有形成抽象概念和形式的普遍性或同一性的能力”。⑥这也正是彻底的经验论走向不可知论的秘密所在。
经验论既然否认了人类有认识无限事物的能力,而将自己局限于感性经验的现象范围,也就失却了获得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基础,尽管经验论大都强调或承认所谓经验有两个成分,即无限杂多的材料与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规定性的形式。但是,“把知觉当作真理的基础,普遍性与必然性便会成为不合法的”⑦。经验并不提供必然性的联系,因为,在经验中固然呈现出很多甚或数不胜数的相同的知觉,但是普遍必然性与一大堆事实的归纳枚举却完全是两回事。经验论的集大成者休谟则干脆宣称,经验中并不包含普遍性和必然性。其实,在黑格尔看来,经验论最致命的缺陷还在于它的所谓的普遍性或必然性的形式,不仅其本身是空洞的,不确定的,“而且是与特殊的东西没有内在联系。两者间彼此的关系也是外在的和偶然的。同样,特殊的东西之间彼此相互的关系也是外在的和偶然的”⑧。经验论的这种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割裂与对立,内容的杂乱无章而缺乏内在联系,用经验材料填充逻辑形式的做法,遭到了黑格尔的严厉批评。
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做法不只是经验论的致命缺乏,也同样是唯理论的致命弱点,康德哲学也未能真正摆脱这种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知识观。因此,在《小逻辑》中,黑格尔在就思想对客观性的三种不同态度的批判中,将康德的批判哲学与经验论放在一起作为思想对客观性的第二态度加以批评。黑格尔认为康德同经验论一样,不仅将人类认识局限于感性的经验范围,而否认了人类认识无限性事物的可能性。而且,实际上也将所谓人类的科学知识图解为先验+经验的公式,既没有真正解决人类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难题(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对人类科学知识可能性的论证,反倒宣判了科学知识的不可能性),同样,康德也没有走出经验论的形式主义的知识论。
那么,要弥补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缺陷,走出传统哲学的阴影,出路何在呢?黑格尔说:“凡是志在弥补这种缺陷以达到真正必然性的知识的反思,就是思辨的思维,亦即真正的哲学思维”⑨。当然,黑格尔认为他自己就是这种真正的哲学思维的代表。黑格尔不仅改造了传统哲学的经验观念,而且也革新了传统哲学的先验观念,由此建立了一种崭新的逻辑学。其间,人类本性、事物的本性通过逻辑、概念的矛盾运动得以展示和实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责编:李秀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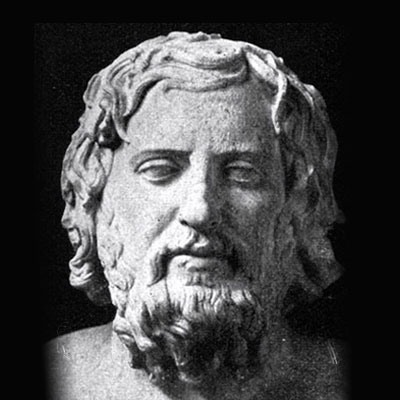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