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生命危险从事暴力活动换来的收益,叫“血酬”。
01 人命有价,良民匪变
生命与生存资源时时刻刻都存在交换关系。买命有几种价格,官府的死刑可以花钱赎买,土匪“拉肥猪、抱童子、请观音”肉票价格有差,军阀以伤亡抚恤金买官兵的命,元太宗以城市产能确定是否对南京和开封屠城。
身外之物在匮乏时也可以“等身”,卖命有其价格。为了保全产业,雇佣农当一年临时土匪可以保数年不愁。海盗集团太平时宁可发放低价路票海票,也不愿冒险抢劫。然而当匮乏突破生死边界,官与匪便再无分界,民与匪也再无区别。
闹荒抗租、焚屋焚仓、抢米分粮有明显的道德合理性,任何产权安排、权利分配在紧急避险的情况下都应被无视。
02 潜流与招待处
除了正式的财税,还有一股潜流从底层流向顶层。超编百倍的衙役依靠合法伤害权力征收陋规,既弥补了微薄收入,也用来应付年年上供的需求。上层官员给顶层的礼金,不是出于升官的需求,却更像是给黑手党的保护费。这种财税潜流是帝国财政的抽水机,将各行各业的资金集中到顶层首官,再贡献给戏剧、工艺品、书画等传统文化事业。
清官海瑞拒绝负担接待和驿站费用,他要求严格照章办事,然而这应付驿站过客的费用就只得由他的上级知府从临县调拨。驿站过客的权益不仅直接表现为要求勒索、间接表现为讨好竞争,还有上级的拨款支持和兄弟单位得力协助。为了获得足够资源支撑接待工作,县官把自己过得更像一个驿丞,像一个招待处处长。作为县官,比起衙役与县丞,他更需要一个黑帮做自己的基层组织。因为欺负百姓无妨,上面听不到,而得罪了过客却要招致诽谤,追求晋升的官员自然知道如何选择了。
03 天下已定,英雄当烹
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里,“聚众”都是重罪。凡是聚众抗粮、罢市、罢考发生时,按<大清律例>是先把为首者斩立决,真正难解决的聚众往往是举人、秀才等熟悉制度的人领导的抗粮。像段光清这样的县官有着完善的分化瓦解策略,让乡民先写请愿书摘清自身,再集中力量抓捕领头“请平粮价”的监生周祥千。周祥千在“怀柔”策略面前,没有选择提高要求、激化矛盾、加入太平军,这使得抗粮队伍的首领陆续被村民扭送官府换取悬赏。
随着动乱扩大,顺民转变为官府眼中的暴民,平粮价的要求就让位于不被镇压的安全愿望。烈火的种子落入湿柴,领头的人才逐渐了解到:
民众没有固定的脸谱,只是始终趋利避害的利益集团,而英雄这种东西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产物,稳定的常规秩序里没有英雄的位置,也不需要英雄。
04 灰牢与合法伤害权
灰牢,也就是非正式监狱,在我国历史上以学习班、小黑屋、黑窑、牛棚、班房等名目出现。主要是集中开会和拘押关禁的分界线太过模糊,这模糊之中产生了一种合法伤害权。
自杀在灰牢里的百姓用自己的一条性命换取的,仅仅是关灰牢官员的处分和死亡抚恤金,看似荒谬,却是明清两代官方认可的命价。在命价低微的时代里,指导官员做事的不是良心与上级,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般对损害的分配。
05 披张虎皮的“硬伙企业”
“灭门的知县,破家的县令”。县官可以在法规范围内让子民倾家荡产,那么当自愿捐助开始时,“帮贴公费”就成了是子民为官府承担开支的一种名目。而公费的去向开支,一个当铺老板怎么可能过问呢?
破坏力要素如同生产要素一般,入伙企业参与分配。商战决定了企业兴衰,而政治往往决定生死。明朝的企业受行政权力支配,也按照入伙等级呈现金字塔结构。
买张虎皮,也就给企业买了对抗相应等级合法伤害权的防御手段。
06 万两白银买面洋旗,值!
清朝末年,全国上下通航的船只纷纷抛弃商船公会的龙旗,以三万白银作“挂旗费”换取外资“虚股”和一面洋旗。哪怕后面偶有被“虚股”强求分红的情况,商人们还是将这笔“挂旗费”列入工商业日常开支中。军阀混战年间,一面洋旗免去了当差和苛捐杂税两项问题。战争年间船只常常被无理由扣押征用,也常被征收各种重复税收,仅扣押一项足以使得航运商破产,这使得中国旗帜被淘汰出局成了时间问题。
法国吉利商行的洋旗有什么用处呢?船只被扣押、税收被重复征收时,洋人确实告,他们的政府确实替挂旗的商人告,告到中央政府外交部,实在不行派军舰护航攻打。驻扎重庆口岸的田团长扣押商船、临时征收军事保险费,最终在军舰压力下,宣布办法只对中国商人生效。
出售公民权利和安全也算是那个时代欧美国家一项产业,这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也是民主宪政中诞生的公民权。这些东西在封建中国里格外值钱,以至于商人愿意购买这项权利。且不说军阀土匪,仅仅是与官吏衙役打交道,一面洋旗就定了企业的盈亏生死。
轮船与中国木船帮的斗争,以官府支持轮船权利告终。就像所有新技术和传统势力的斗争一样,洋旗支撑的发达国家公民待遇超出了中国公民待遇。技术优势转化来的待遇优势,也使得业务上锦上添花。
这面洋旗和它代表的公民权利与制度带来的收益,叫做“法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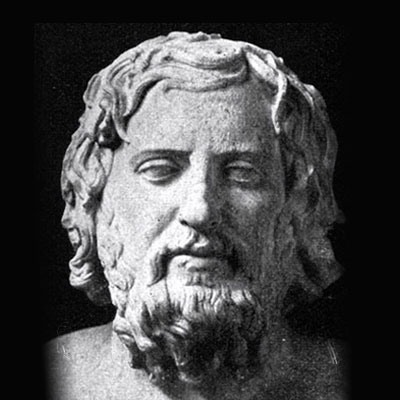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