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Hayek’s Monetary Theory and Policy: A Critical Reconstruction,原载于《货币、信用与银行》(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1999年,第31卷,第1期。链接见文末。
作者简介:伦斯·H·怀特(Lawrence H.White)现为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曾任纽约大学、佐治亚大学和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教授,专注于银行与货币的理论与历史,现担任梅卡图斯中心的哈耶克哲学、政治和经济高级研究项目杰出高级研究员。
译者前言:奥地利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停留在货币起源的理论争议阶段,始终坚持抽象价值作为货币前提的立场。后续更新文章会详细讨论马克思以及门格尔的价值、货币概念。至于大学课堂上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货币和银行的世界中。
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剑桥资本争论—即不同实物如何被概念化为相同形式的抽象资本概念,参见:奥地利学派与剑桥资本论战。但是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对于货币的论述,依然没有脱离门格尔的演绎框架:即设想「最可售商品」会逐渐获得媒介地位。在这一推导过程中,货币在先前交易中已经产生。后续交易只是执行先前交易的结果。这一概念存在双重局限性:门格尔的个人主义演绎推理概念使得国家范畴下的统一货币变得难以理解;更为严重的缺陷在于,门格尔的交易同时忽略了延时交付—时间;服务与实物的交换—所有权交易等现实情况。哈耶克未能成功的逃离这一演绎逻辑框架,使得他最终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
正如康芒斯所言:「财产权本身包含商品的两种矛盾的意义,即有形的物质和物资的所有权。古典经济学家的卓越的著作之所以调和一致,完全是因为他们本身内含的矛盾是看不出的。直到1840年至1860年二十年中,从正统学派的这种基本矛盾中产生四派非正统的经济学家时,这一矛盾才显得很突出。普鲁东把这种矛盾转换为无政府主义,马克思把它变成共产主义,凯雷和巴斯夏把它变成乐观主义,可是,麦克劳德采取了商品所有权那方面的意义,把商品的物质的意义放在生产论和消费论里面去。」——《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康芒斯著,于树生译。
摘要
哈耶克对价格水平稳定化的批评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只有恒定的货币存量(M)或恒定的名义支出量/货币交易总量(MV)才能允许跨期价格均衡。这一观点通常并不正确。因此,哈耶克原则上为恒定名义支出量所做的论证,以及他批评自动金本位制未能实现这一点的观点,都缺乏说服力。他的商业周期理论中的注入效应为其主张提供了另一个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哈耶克转而支持价格水平稳定化。在这样做时,他在逻辑上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1899-1992)是凯恩斯革命前夕专业领域内领先的货币理论家之一。关于货币、资本和商业周期的早期工作目标,用哈耶克自己的话说是「将周期现象纳入经济均衡理论体系,而这些现象与均衡理论表面上是矛盾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曾评论说「很可能许多现代经济学家会毫不困难地接受哈耶克对这一问题的表述,认为它大致相当于他们自己的观点」。
虽然近年来哈耶克的著作普遍受到相当多的批判性关注,特别针对是他的商业周期理论,但他基础的货币和银行理论却未受到同等重视。在此,我对哈耶克关于货币经济中跨期价格均衡条件的分析进行重构和批判,并评估其据此提出的货币政策主张。我发现哈耶克得出的一个关键结论——维持跨时货币均衡需要恒定的名义支出量——在他自己的完美预见假设下并不成立。因此,他批评金本位制未能维持恒定名义支出量的论点缺乏充分依据。哈耶克反对价格水平稳定政策的另一个可能更有说服力的基础是他的商业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在预见不完全的条件下,货币注入会扭曲跨期资源配置。
哈耶克的恒定名义总支出量准则有助于解释他对自由银行业和金本位制*的矛盾态度,这种态度原本令人费解。他的导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曾强烈支持这些制度,而哈耶克自己在其他地方也视自由竞争和演化形成的市场制度为社会协调不可替代的手段。但在后来陈述指导其早期理论构建的愿景时,哈耶克宣称「所有时代的所有货币」,无论其供应体制如何,都是「市场自我调节机制中的一种松散连接」。
*金本位制在经济增长时会产生长期通缩,前提是黄金的长期存量供应曲线不完全平坦,且需求曲线随时间向右移动的速度快于供应曲线,这种情况可能因采矿的资源耗竭效应而发生。Rolnick和Weber发现,金属本位制在历史上表现出温和的长期通缩:通货膨胀率平均约为每年-0.5%。【类似的情况在银本位制下同样出现,参见徐谨《白银帝国》中对明清货币史的简要梳理】
跨期均衡与价格水平稳定化的批判
哈耶克早期的工作,直至《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 1931)一书,旨在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货币政策主张提供理论基础充分的批判。价格水平「稳定者」主张中央银行应随实际产出增长而扩大货币存量,而不是像在货币存量恒定或自动金本位制下的增长经济体那样让价格下跌。在《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英译本的新序言中,哈耶克指出「对『稳定者』计划的批判,从很多方面来说是本书的核心主题,已经占据了我多年的思考」。哈耶克关于跨期价格均衡的分析为其批判提供了理论基础。
价格水平稳定化计划的错误不仅仅是抽象的理论问题。哈耶克认为,这一计划在1925年至1929年间激发了英格兰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进行有害且最终徒劳的货币扩张联合行动,试图阻止因英国黄金外流和美国经济实际产出快速增长而应随之而来的价格下跌。哈耶克随后认为1929-32年的深度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反应。
哈耶克的理论批判认为,为稳定价格水平而改变货币数量必然会破坏生产经济中实现跨期均衡所需的相对价格关系。要论证稳定化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扰乱了英国和美国经济,哈耶克只需证明这与中央银行同时对金本位制的承诺相冲突。但在1928年的一篇关键文章中,哈耶克提出了更为全面但不那么容易辩护的论点:在任何货币制度下,任何货币数量的变化都会造成失调:
「只有在货币系统排除任何货币数量变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构想出一种在连续时间点上建立的货币价格结构,与跨期均衡系统相对应。」
哈耶克未能成功证明这一论点,因为这种过于笼统的表述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在固定汇率商品本位制之外的情况下,名义货币和价格的变化并不必然导致实际变量偏离跨期均衡的一致值。
哈耶克旨在证明,当两个时间点之间的预期整体生产率(或预期实际生产成本)不同时,预期价格水平需要有所不同,以允许在两个时间点之间实现产出的均衡配置。他通过三个明显需要相对价格差异才能达到均衡的案例来构建论证。首先,如果两个地点在比较优势上有差异,使得一个地点能够更廉价地生产鸡蛋(哈耶克的例子),那么假设运输成本为正,均衡时两地的鸡蛋价格必须不同。其次,如果夏季生产鸡蛋比冬季更便宜,假设储存成本为正,均衡同样要求鸡蛋价格存在季节性差异。第三,如果正确预期到鸡蛋行业的技术进步相对迅速,使得未来鸡蛋生产成本更低,那么跨期均衡要求鸡蛋相对价格预期会下降。如哈耶克所论证的,阻止任何这些情况下的均衡价格梯度都会导致供需不匹配。
哈耶克随后将分析转向总体水平。考虑一个只有两种明确商品的经济体,即在两个时间点上的复合消费品和货币。哈耶克论证认为,为了生产的跨期均衡,如同上述第二和第三种情况,消费品的(预期和实现的)货币价格(即「价格水平」)在消费品行业产出较高的日期必须较低。如果生产率随时间增加,「对价格不变的预期会导致未来相对于当前供给的产出过度增长」。
哈耶克跨期价格均衡论证中的缺陷
哈耶克的论证在固定金本位制下完全正确。消费品相对于黄金的边际成本下降意味着黄金的相对均衡价格上升,因此以固定黄金含量的美元计量的价格水平下降。固定金本位制会自动产生这一结果,尽管哈耶克认为不是这样(见下文)。
但这一论证并不适用于所有可能的货币制度。哈耶克未能区分货币单位价值的实际变化和纯粹名义变化。在「可调整」的金本位制下,美元数量和价值原则上可以在不扰乱实际变量的情况下改变,方法是调整美元的黄金含量(例如,贬值)并适当重新调整所有名义价格和债务合约。这种贬值就像仅仅从盎司转换为克的计量单位变化。同样,在法定货币制度中,在比较静态思想实验中,货币数量和价值也是纯粹的名义变量。每个代理人的法定货币余额和所有货币价格(包括债务)的比例变化仅构成经济名义标量的中性变化。
在两期经济中,如果代理人在跨越两个时期的合约和计划中正确预期并「看穿」了货币存量和价格在第二期的参数变化,跨期交换和生产的均衡是可能实现的,这与哈耶克声称必须排除任何货币存量变化的笼统论断相反。对于非指数化的贷款合约,这意味着需要在名义利率中加入通胀溢价,使实际利率保持在均衡值。对于跨期生产计划,这意味着要用实际(适当贬值后的)投入和产出价格而非仅仅是名义价格来计算利润。
在法定货币世界——一种基础货币,对非货币用途没有需求,且生产名义单位的边际成本为零——消费品的均衡比较成本和相对价格(相对于货币商品)的概念不再适用。正如吉尔伯特(Gilbert)所论证的,在假设每个未来日期的价格水平都被正确预期的前提下,在法定货币制度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唯一与跨期均衡一致的价格水平路径。正确的通胀溢价原则上可以纳入跨期货币计价合约和生产决策中。名义利率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以允许在预期法定货币购买力不同的任何一对日期之间建立正确的货币交易条件。哈耶克认为在生产率提高的世界中,稳定的名义价格水平必然会扰乱生产决策的论点,暗示生产者在决定生产日期时比较的是未折现的名义销售价格。这种决策规则只有在跨期货币兑换比率固定为1:1时才合适,即名义利率固定为零。尽管哈耶克引用了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但他未能协调其观点与费雪对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区分的观点。
在法定货币制度下,同时假设实际利率为正和货币存量增长刚好足以维持稳定价格水平并无内在矛盾。因此名义利率不固定为零。但这些假设与金本位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黄金生产者行为是否一致?面对正利率,为什么有人会持有不增值的原地黄金而不是开采所有已知储备并投资收益?正如罗科夫(Rockoff)指出,在适当条件下,「霍特林法则」适用:在完美预见的竞争均衡中,假设稳定且不变的开采成本,未开采黄金单位的价值必须按所有者本可获得的实际利率随时间增长。给定正实际利率,以黄金计量的价格水平必须以实际利率下降,验证了名义利率为零的假设。然而,霍特林法则的条件不必然成立,历史上也确实不成立。边际开采成本上升且随时间下降,因此尽管黄金增值率低,推迟部分开采仍有利可图,还有意外的黄金发现。在历史金本位制下,名义利率始终为正。
在法定货币制度下,不止一种价格水平路径允许跨期均衡,因为名义利率可以相应调整,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均衡中的实际变量都相同(即法定货币「超中性」),也不意味着在法定货币制度下没有相关理由偏好一种价格水平路径(或通胀率)而非另一种。主要相关考虑因素应该是:(一)一条路径能被正确预期的难易程度,(二)与维持该路径的货币政策相关的注入效应,(三)名义价格的「噪声程度」,(四)调整价格和/或名义刚性的成本,以及(五)沿该路径持有货币的成本。这些是哈耶克在其商业周期理论中确实强调的问题。
货币政策准则
从他过于笼统的主张「货币总量的变化永远不可能有助于维持均衡,相反必然会破坏均衡」,哈耶克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原则上冻结货币数量造成的失调最小。尽管他在其他地方以尊重自发演化的市场制度所蕴含的智慧而闻名,哈耶克批评金本位制,因为它允许货币黄金数量变化。他同样批评自由银行业,因为它允许银行发行货币的数量变化。
哈耶克对金本位制的批评实际上并不源自他对跨期均衡的关注。诚然,在上升或变动的黄金存量供应曲线下形成的货币价格路径与黄金存量永久固定情况下的路径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跨期均衡必然被扰乱。只要合约双方正确预期黄金购买力的短期和长期变动,正确的通胀溢价可以纳入跨期货币合约中。如果黄金生产者有正确的预期,黄金存量和黄金与消费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将按照跨期均衡所需的方式变动。相比之下,保持货币黄金数量不变通常与黄金生产的均衡不一致。
哈耶克1928年关于固定货币量的跨期均衡论证不成立,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支持固定货币量的充分理由,更不意味着没有理由支持稳定名义总支出量。这仅表明相关论证需要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一个合适的基础应该是证明货币注入会扰乱实际或感知到的当前相对价格(而不仅仅是当前与未来名义价格之间的关系)。虽然哈耶克1928年反对价格水平稳定化的论证并不基于注入效应或公众对价格的不完全预见,但这些因素对他在20世纪30年代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至关重要(它们的重要性在哈耶克1939年的论述最为明显)。在哈耶克(1931)的周期理论中,未预期到的货币注入暂时将市场利率降低到长期均衡水平以下——或者银行系统在贷款需求和均衡利率上升时扩大信贷而非提高贷款利率——扭曲了资本品相对于消费品的价格。另外,在卢卡斯(Lucas)的理论中,改变价格水平的未预期注入导致代理人错误地推断相对价格和实际工资可能已经改变。
在1928年的论文中,以及1929年对福斯特-卡钦斯(Foster-Catchings)价格水平稳定化方案的批评中,哈耶克提出在产出增加(例如,由于技术改进或净资本形成)的情况下,应保持货币存量不变,并允许价格水平下降。在这些早期著作中,哈耶克并未明确考虑除产出量变化外,改变货币总量的其他理由。但他那笼统的主张「货币总量的变化永远不能有助于维持均衡,相反必然会破坏均衡」实际上排除了所有其他理由。
在《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无论是1931年第一版还是尤其是1935年第二版)中,哈耶克承认他「政策的原始准则,即货币数量应保持不变」存在一个重要例外。他之前「排除了流通速度变化的考虑」,但交易速度的变化「一直被正确地视为等同于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变化」。因此,「如果货币要对价格保持中性,流通速度的任何变化都必须由流通中货币数量的相应反向变化来补偿」。
哈耶克显然推理认为,速度变化就像货币存量变化一样,会通过导致价格水平的变动偏离生产成本的变动而扰乱跨期均衡。因此,哈耶克将他修订后的货币政策准则表述为不是货币存量(M)的恒定,而是「货币总流量」的恒定,即货币存量乘以其流通速度(MV)。
在从恒定货币量转向恒定名义总支出量准则后,哈耶克相应地调整了对金本位制的批评。现在强调的是流通速度V的变化(货币供应量M应迅速响应以稳定名义总支出量),而非商品产出的变化(M仍然不应对此做出反应),哈耶克现在宣称黄金的供应弹性是一种优势而非缺陷。金本位制的主要缺陷现在被认为是黄金存量对货币需求变化的反应速度不足。哈耶克批判性地指出,对于黄金价值上升的反应,黄金数量在短期内的变化远小于长期变化。但当立即进行全面调整成本更高时,黄金数量的渐进调整实际上是完全适当的。
哈耶克强调,恒定名义总支出量准则适用于整个统一的货币经济体,而非任何区域子集,如国际金本位制下的单一国家。任何区域货币存量的弹性是可取的,因为维持区域间均衡,考虑到各地区相对货币需求的变化(例如,由于它们在世界收入份额的变化),需要货币余额的区域间重新分配。纯粹的国家货币政策,特别是价格水平稳定化政策,将与区域间均衡所需的货币全球重新分配相冲突。
世界货币机构或金本位制?
哈耶克指出,在多国货币区实施恒定名义总支出量准则需要「全球中央货币管理机构」,或者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政策协调机制,以抵消货币量(源于货币乘数变化)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他强调,除了建议在繁荣期和萧条期都对货币扩张保持更大的克制外,该准则并未为受国际金本位制约束的国家中央银行提供「货币政策的实用准则」。然而,哈耶克对通过建立世界货币管理机构来改善货币政策的前景并不乐观。金本位制确实倾向于使价格水平回归稳定的长期轨道,这使名义价格比在实际替代体系下更具可预测性。他警告说,试图「彻底重构我们的货币体系,特别是用或多或少任意管理的货币来替代半自动的金本位制」所带来的危险「远大于金本位制可能造成的损害」。在哈耶克看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际经验无疑证实了这一警告。
由于哈耶克拒绝将价格水平稳定作为理想目标,他不同意普遍认为大萧条的困境应归咎于金本位制的通缩倾向的观点。相反,世界经济的失调是中央银行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受价格水平稳定理念启发,拒绝了纪律并破坏了金本位制的运作。尽管哈耶克认为金本位制相比于他理想中的「整个世界范围内或多或少恒定的货币流通量」是次优选择,但只要「真正合理的货币政策仍然是一个乌托邦梦想」,「任何机械原则(如金本位制)」至少具有在国家间分配全球货币存量的均衡机制,这就有其价值。因此,哈耶克对金本位制的整体评价是矛盾的:「如果它没有提供真正合理的货币数量调节,它至少倾向于使货币行为大致可预见,这是极其重要的。」哈耶克后来支持多种商品储备货币,作为保留黄金优势同时避免他所认为的剩余缺点的方式。
货币的非国有化
哈耶克在1943年关于商品储备货币计划的文章与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之间的三十多年里,几乎没有撰写关于货币的文章(除了1960年《自由宪章》中的一章)。在他关于货币政策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货币的非国有化》(The Denationalisation of Money)中,哈耶克出人意料地放弃了货币流量恒定作为准则,转而接受消费者价格水平稳定作为综合考虑下最理想的货币准则。他主张允许私营企业发行法定型货币,主要理由是竞争性发行者系统比中央银行能更有效地实现价格水平稳定。
哈耶克呼吁稳定某种价格水平并非完全没有先例。早在1933年,哈耶克就提出,在流通速度冲击是个问题的现实世界中,「稳定一些原始生产要素价格的平均值可能为货币数量的有意识调节提供最实用的准则」。以原材料和其他投入品价格指数为目标将允许最终产出(消费者)价格随生产率提高而下降,这样就能近似哈耶克所追求的跨期名义价格关系。在《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中,哈耶克曾支持「某种综合价格水平的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而非就业目标,但他担忧目标指数「不应仅指最终产品(因为如果这样做,在技术快速进步时期可能仍会产生显著的通胀倾向)」,即可能要求显著的货币扩张。
然而,在《货币非国有化》中,哈耶克论证了最终产出价格水平稳定或零通胀的协调特性。他放弃了早期观点,即阻止名义产出价格下跌会系统性地造成跨期资源错配。他现在认为:(一)可预测的通胀率促进长期合约的协调;(二)零通胀率使相对价格预测错误最小化,因为在给定时期内许多价格不变;(三)需要「相当稳定」的记账单位来实现「有效的资本维护和成本控制」。总之,稳定价值的货币因「预见、计算和会计」原因而更可取。
根据哈耶克现在的理解,服务货币使用者的偏好需要货币发行者必要时操纵其数量以稳定其购买力。他在20世纪30年代曾指出,这种政策(当时他反对这种政策,除非是为了应对流通速度冲击)对受金本位制约束的中央银行是不开放的。他现在注意到,这对私人发行的可兑换黄金的货币也是不开放的。因此,哈耶克预测,在不同类型货币的自由竞争中,公众会选择稳定价值的私人法定型货币而非商品货币。
无论其预测有多可疑,《货币的非国有化》都有一个优点,即大胆地将货币政策的辩论重新构想为更为根本的货币制度辩论。哈耶克放弃了寻求理想的中央银行政策,转而支持更为一贯「哈耶克式」的观点,即理想的中央银行政策是不可实现的,其原因与理想的中央计划不可实现大致相同。哈耶克认识到,即使由私人发行者执行,为稳定货币价值而注入和收回货币的政策也会引发非中性注入效应问题,这一问题是他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在一个引人注目的转变中,他现在认为这些效应微不足道:
「即使在增长经济中为保证价格水平稳定而必须增加的货币数量也可能导致投资超过储蓄。但尽管我是早期指出这一困难的人之一,我倾向于相信这是一个实际意义较小的问题。」
如果要接受消费者价格水平稳定,哈耶克在逻辑上必然要这样做,他在此基本上否定了他早期的商业周期理论及其所有基础,最重要的是他将大萧条爆发(很难说是「一个实际意义较小的问题」)解释为20世纪20年代中央银行稳定化实验的必然后果。他没有指出应该用什么周期理论来取代它。在这一关键方面,《货币的非国有化》与哈耶克早期的著作有着根本性的决裂。哈耶克转变为价格水平稳定的支持者对未来研究提出了一个谜题。
结论
哈耶克1928年关于跨期价格均衡论证的有效核心是,价格水平稳定与维持固定黄金平价不相容。与哈耶克的暗示相反,该论证既不能作为批评金本位制自动运作的基础,也不能作为在法定货币标准下拒绝价格水平稳定的理由。为了证明哈耶克支持的恒定名义总支出量货币政策准则的合理性,人们可以论证货币注入会扭曲相对价格,这需要放松他1928年的完美预见假设。对于纯名义价格传递错误信号,有理由认为代理人必须面临信号提取问题。在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中,注入效应和信号提取问题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他确实独立地为他在法定货币标准背景下对价格水平稳定的批评提供了分析基础。在其职业生涯末期,哈耶克出人意料地从批评者转变为消费者价格水平稳定的倡导者,他不得不否认其商业周期理论的实际相关性。
引用及注释略。
Lawrence H.White 拉斐尔的低语 2025年03月22日 01:32 美国
https://mp.weixin.qq.com/s/7WvfhZn-F3rOfeBh4Mu2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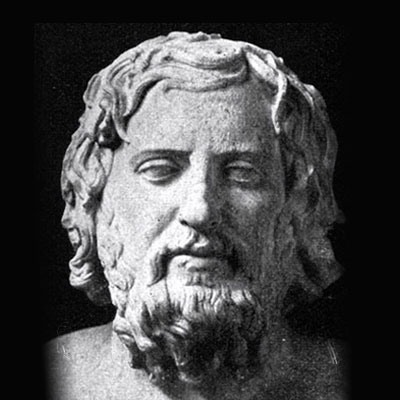
0